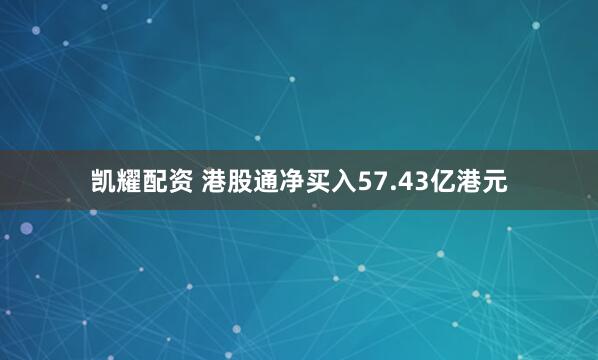海报新闻首席记者 张稳 解强民 记者 文露漪 报道
今年8月,芳若的头部被植入了仅有硬币大小的脑机接口处理器和用来采集脑电波的电极。一个月后,脑机接口开机,她的脑电信号被机器读取出来,传达给气动手套。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芳若用戴着手套的右手抓起了一个水瓶!此时,距离她因车祸致瘫痪,已经过去了6年。这些年,从她大脑产生的运动意念,几乎无法再传达给躯体。
在我国,像芳若这样因车祸、外伤等原因导致脊髓损伤的患者约400万人,每年新增约9万人,其中85%为中青年人。脊髓神经受损让大脑失去了对肢体的掌控,患者被“困”在了自己的身体里。此前,医学界始终未找到有效的治疗手段,直到一项运用脑机接口技术的神经外科手术的出现,僵局似乎才被打破。一些原本全身瘫痪多年的患者在接受“脑机接口手术”后,竟能够弹钢琴、玩游戏、操控轮椅了。
然而,这项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手术,其背后的原理是什么,真有那么神奇吗?从试验到大规模临床应用,还有多长的路要走?近期,海报新闻记者走访湖北、河南、山东等地的多个患者家庭、医院门诊,拜访多位权威专家,试图找到答案。
9月24日,正在进行居家脑机接口康复训练的芳若。
“假如能重新站起来,
哪怕只有一丁点儿机会也要试一试”
提到脑机接口,许多人可能会想到全球首富马斯克。2024年1月,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的脑机接口公司已为首位人类患者植入了大脑芯片,引发巨大轰动。
2025年年初,瘫痪6年、只有手臂能轻微活动的芳若,开始频繁刷到介绍“脑机接口手术”的短视频。
“要在病人的大脑植入一个芯片,芯片与神经、外骨骼相连接,病人可以用意念来控制外骨骼。”芳若对于手术的理解仅限于此。
虽然不太明白深层原理,但在看到有医院招募脑机接口临床试验志愿者时,芳若立刻就决定报名。原因很简单:像她这样的高位截瘫患者,医学界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所谓脑机接口(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BCI),其原理是在人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起实时通信与控制系统,既可以解读脑部信号、控制外部设备,也可以将信息编码输入大脑,实现生物智能与机器智能的协同交互。
人类对脑机接口的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直到二十一世纪半导体等电子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脑机接口技术的应用场景才开始大幅拓展。例如,2014年,在巴西世界杯上,截肢残疾者凭借脑机接口和机械外骨骼开出第一球;2023年,在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上,一位失去左上臂的运动员,凭借“意念”操控着智能仿生手,完成火炬点燃。
打定主意做手术后,芳若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寻找跟她有相似经历的病友,来自云南的小佐就是其中之一。小佐今年29岁,2022年因意外受伤而高位截瘫,日常生活全靠家人照顾。今年5月,小佐看到医院招募脑机接口临床试验手术志愿者的信息后,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在6月接受了手术。
家人在设备的助力下把芳若从轮椅上拉起来。
记者注意到,在谈及脑机接口手术时,芳若和小佐都提到了一个人——老杨。
2023年10月,四肢瘫痪14年的老杨在宣武医院接受了脑机接口手术。根据公开报道,这是我国首例无线微创脑机植入手术。在手术台上,老杨的颅骨被凿开一个小孔,置入了仅有硬币大小的脑机接口处理器和含有8个接触点的电极。术后,通过脑电活动驱动气动手套,老杨恢复了自主喝水等脑控功能。
同年12月,35岁的截瘫患者小白在天坛医院接受了这项手术。小白因车祸造成脊髓损伤,通过体内机和植入的电极,脑机接口得以成功解析他的脑信号。
上述患者使用的脑机接口设备,均为清华大学洪波教授团队研发的无线微创脑机接口NEO。该团队在2020年展开了动物实验,验证脑机接口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于2023年在宣武医院和天坛医院分别通过了伦理审查,首次进入小规模的临床试验阶段。
对于像芳若和小佐这样的高位截瘫患者来说荣利通,老杨的故事让他们看到了恢复运动能力的希望。“这些年,能试的都试过了,就算长年累月坚持康复训练,也没有什么明显变化。”芳若直言,“假如能重新站起来,哪怕只有一丁点儿机会,也要试一试,不管有什么风险。”
“我的手又回来了!”
脑机接口手术助多例瘫痪患者“动起来”
8月14日,芳若在宣武医院接受了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一个月后,脑机接口开机,她的脑电信号被机器读取出来,传达给气动手套。已经瘫痪6年的她,终于靠着自己的“力量”抓起了一个水瓶。
这神奇一幕的背后,是多年科学研究和试验的支撑。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以下简称“千佛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李锋告诉记者,大脑在思维活动时产生脑电波,我们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接受大脑的指令,一个人如果不能有效接收或执行大脑指令,就会出现语言、行动或者视力障碍。脑机接口手术的作用过程,就是通过大数据对比,把采集到的脑电波的波形、波幅、频率进行解码、识别,再转化成指令性的机械驱动。目前,大家较为熟知的脑机接口的连接方式主要有侵入式、半侵入式、非侵入式以及介入式。

7月15日,山东省首个专注于脑机接口(BCI)技术的临床研究病房在千佛山医院正式揭牌启用。
芳若、小佐和老杨接受的是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又称“开颅不入脑”,是将电极植入颅骨下方、硬脑膜上方,置于大脑皮层表面进行脑电信号采集。
“我的手又回来了,可以自己喝水了!”当芳若在北京接受手术时,58岁的高女士头戴脑信号采集器,凭“意念”驱动控制气泵手套,稳稳地完成了抓握并移动水杯。
今年6月28日,因车祸导致高位截瘫的高女士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成功接受了华中地区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手术历经两个多小时,同济医院神经外科舒凯、胡峰医生团队在神经外科机器人导航下,将两根电极精准植入到高女士的左侧脑部硬膜外手部运动和感觉区,同时在皮下埋藏一枚1元硬币大小的记录设备,不触碰脑组织即能捕捉大脑与手部运动的神经信号。
同济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脑机接口研究院院长唐洲平介绍,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搭建一条“信息高速公路”,通过解码大脑运动意图信号来绕过受损的神经通路,再通过外部设备的闭环康复训练,可以有效重塑神经功能,进而促进运动功能的恢复。
2025年被业界视为脑机接口行业的“元年”。越来越多的脑机接口手术成功案例被报道出来,让无数患者和家属对其充满憧憬。
今年3月,宣武医院成功为一名67岁的渐冻症患者完成全球首例“无线植入式中文语言脑机接口”手术。术后,置入患者大脑语言区的高密度电极,能实时采集患者的“内心所想”,让失语的患者恢复了一定的语言交流能力。
6月,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联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开展了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临床试验。这标志我国在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上,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国家。仅用2周至3周的训练,受试者就可借助脑机接口系统,玩象棋、赛车游戏,达到了跟普通人控制电脑触摸屏相近的水平。
同样是在6月,全球首例介入式脑机接口辅助人体患肢运动功能修复试验在我国完成。受试者是一位因脑梗死导致左侧肢体瘫痪半年的67岁男性患者。项目团队在高精度DSA影像引导下,通过颈部血管介入微创手术方式,将支架电极导入到患者相应的颅内血管壁,并将无线传输与供电设备植入患者皮下,从而实现脑电信号采集与信号的无线通信传输。
6月28日,同济医院成功完成了华中地区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
科幻能否照进现实?
脑机接口手术距离临床应用仍任重道远
脑机接口手术的效果如何?从上述案例的相关报道中以及临床试验志愿者的描述中可见一二。
芳若在接受手术一个多月后,已经能够通过“意念”控制手套,对物品进行抓取,只是动作略显笨重、僵硬。
术后四个月的小佐则表示,经常进行训练的右手在灵活性、力量等方面变得更好了,其他方面暂无明显的改变。
他们明白,这项手术最主要的作用是通过控制外部设备驱动僵硬的肢体“动起来”。但他们还是忍不住期待,希望通过手术和持续锻炼,将来有一天自己瘫痪的肢体能真正恢复运动能力。
芳若和小佐渴望达到的效果,正在老杨身上一点点实现。经过一年半的脑机接口训练,如今老杨已经可以徒手完成吃饭、喝水等动作,他的脊髓神经连接在不断改善。
对此,李锋解释说,不排除有患者在接受脑机接口手术后,实现部分神经的再生修复。“但顾名思义,脑机接口手术的重点是‘脑’和‘机’,最主要的还是借助机械臂、外骨骼让瘫痪患者动起来。这个手术没有那么神奇,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适合做,更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神经再生修复的效果。”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发布《神经系统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其中专门为脑机接口新技术价格单独立项,设立了“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费”“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出费”等价格项目。各地落实立项指南后,脑机接口医疗收费将有规可依。当月,湖北省医保局发布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医疗服务价格。
这意味着,一旦脑机接口技术成熟,手术快速进入临床应用的服务收费路径已经铺好。
9月25日,正在进行居家脑机接口康复训练的芳若。
但是,这项手术距离成为一种成熟的“治疗手段”,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采访中,多位神经外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告诉记者,脑机接口手术目前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其实际效果、手术标准、适用人群、长期风险(如感染、排异等)等方面存在诸多未知,缺乏统一标准,需要进一步积累病例数据、验证其安全性与有效性,不能盲目夸大手术作用。
此外,患者并非做完手术就能“一劳永逸”,还需配合外骨骼设备、电刺激以及长期训练才能获得更好疗效。不止一位专家向记者表示,在神经外科领域,脑机接口手术本身的操作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有效收集脑信号并进行精准解码。
千佛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周朋告诉记者,目前人类对于大脑的认知还比较有限,准确识别脑电波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植入人脑的电极属于异物,容易引发人体免疫反应,形成疤痕组织,从而导致信号衰减甚至使设备失效,影响对大脑活动的准确解读和控制。
洪波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的脑机接口水平还做不到完全解读大脑的神经信号和信息,距离实现“读脑”还有很远的距离。从最早的人工耳蜗,到最新的脊髓刺激器、脑起搏器等,广义的脑机接口已经应用于许多疾病的治疗中。但是聚焦于大脑神经信号采集翻译的脑机接口,目前还没有走进临床。
同济医院脑机接口咨询评估门诊。
10月11日,记者在同济医院脑机接口咨询评估门诊见到了50多岁的李丽(化名)。这是她第二次来医院,主要是做无创脑机接口临床试验前的数据采集。她和丈夫在网络上看到脑机接口技术,期待参加测试后能够实现生活自理。“网友把脑机接口技术说得很牛,很多病友也抱着很大期待。但我知道没这么快,一个技术不可能刚研究出来就能让瘫痪病人站起来。”
在门诊室外,有不少和李丽一样前来咨询的患者和家属。自6月5日开设脑机接口评估门诊以来,同济医院已接诊和评估来自内蒙古、山东、江苏等全国各地的患者200余人。
在北京天坛医院,自今年3月开设脑机接口评估门诊以来,已接到800多位患者预约。所有患者都试图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但真正能做脑机接口手术的人却不多。同时,这项手术究竟能否真的让瘫痪者走路、失语者说话,还有待时间和数据证明。
盈富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